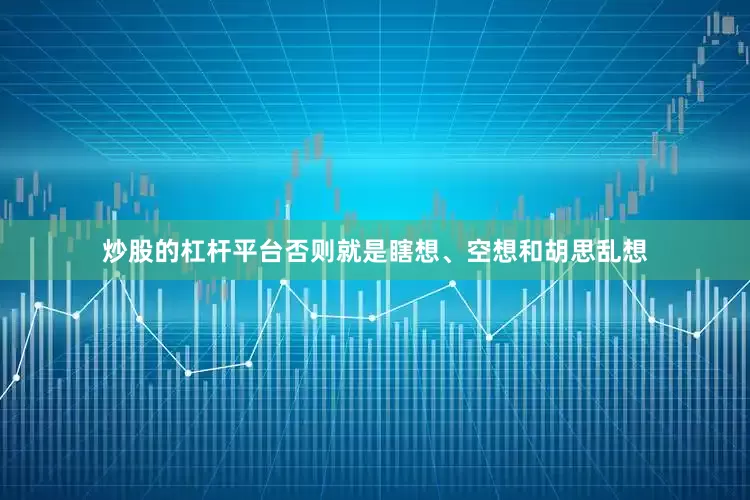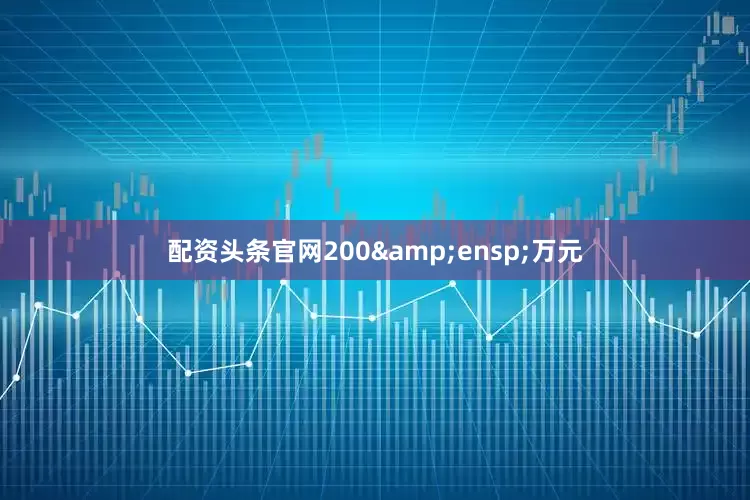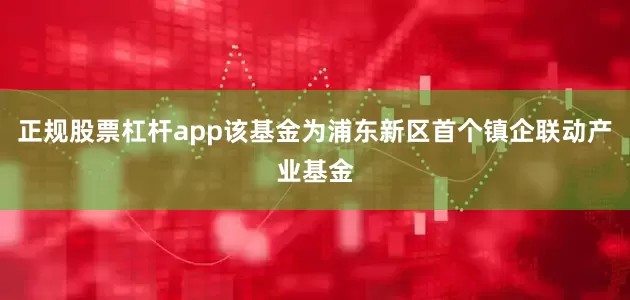莆田 “壶兰文化” 以壶公山的厚重、木兰溪的灵动为底色,融农耕文明的务实、海洋文化的坚韧于一体,更藏 “崇文重教、忧乐为民” 的精神内核。莆田籍作家张元坤在《律中寄潮》中,并未直白堆砌 “壶公山”“木兰溪” 的地域符号,而是将 “壶兰文化” 的基因拆解为山水意象、民生关切与精神品格,融入七言律诗的格律框架,实现了地域特色与普遍情怀的深度统一,为地域文化的古典诗性转化提供了鲜活样本。
一、山水意象:壶兰风貌的诗性复刻与文化隐喻
诗集中的山水书写,是对莆田 “壶兰胜景” 的具象描摹,更是对地域文化气质的隐喻性表达。木兰溪作为莆田的 “母亲河”,其水乡特质在诗句中随处可见:《柳岸春笺》“翠柳含烟映画屏,燕语唤春韵初鸣”,“翠柳含烟” 勾勒出木兰溪畔春日雾霭朦胧的水乡景致,“燕语唤春” 则暗合莆田 “水绕村郭、禽鸣田畴” 的农耕生态;《三月春景》“柳线垂青抚碧川”,“碧川” 直指木兰溪的澄澈,“柳线抚川” 的轻柔笔触,恰如溪水滋养两岸的温润,藏着莆田人对母亲河的依恋。而壶公山的厚重,则化入《观化》“四时流转岁华迁,草木荣枯自有天” 的哲思 —— 壶公山作为莆田人眼中 “定山”,见证四季更迭、岁月变迁,诗人借 “草木荣枯” 的自然规律,暗承壶公山所象征的 “沉稳守常” 的地域品格,让山水意象超越 “风景记录”,成为地域文化的 “诗性符号”。
展开剩余74%更精妙的是,诗人将莆田 “农耕与海洋共生” 的文化特质,融入田园图景的书写。《油菜春光》“金波涌浪连阡陌,翠色铺茵接野桥”,“金波涌浪” 既写油菜花田的壮阔,又暗合莆田沿海 “潮汐涌岸” 的海洋记忆;“阡陌”“野桥” 则是农耕文明的典型符号,二者并置,恰是莆田 “山海相依、耕海并存” 的地理文化特征的诗性呈现。这种 “农耕意象藏海洋记忆” 的书写,让地域风貌不再是孤立的 “乡土符号”,而是承载着文化记忆的 “活态载体”,读者既能从 “金波连阡陌” 中看见莆田春日的田园美,也能读出莆田人 “既守田畴、亦向沧海” 的生存智慧。
二、民生关切:壶兰 “忧乐为民” 传统的当代延续
“壶兰文化” 的核心,始终含着 “以民为本、忧乐与共” 的精神,这在诗集中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与基层治理的反思中体现得尤为鲜明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莆田人,张元坤深谙本土民生痛点,其诗作中对 “折腾”“缺德” 等现象的批判,本质是对莆田 “务实为民” 传统的坚守。《折腾》“朝令夕更田事废,挖填往复庶民殃”,看似泛写政令反复之害,实则藏着对莆田农村发展的关切 —— 莆田多丘陵、耕地珍贵,“田事废” 直接触及农民生计,“庶民殃” 更是直指政策摇摆对基层百姓的影响,这正是对莆田传统中 “为官当恤民” 理念的当代回应。
而《感世》“人心藏险暗无光”“旧雨投井下石处” 的痛斥,虽未明指地域,却暗合莆田 “崇文重教” 传统下对 “道德秩序” 的珍视。莆田历来有 “文献名邦” 之称,“崇文” 不仅是尚学,更是重德,诗人对世态冷漠、道德失序的批判,本质是对本土 “重德崇文” 文化基因的捍卫。这种 “以诗为谏” 的民生关切,让 “壶兰文化” 的 “忧民” 传统脱离了历史语境,转化为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应 —— 既带着莆田人的 “乡土关切”,又具有 “为民发声” 的普遍意义,实现了 “地域情怀” 与 “公共关怀” 的同频共振。
三、精神品格:壶兰 “务实坚韧” 基因的格律化表达
莆田人 “务实坚韧” 的品格,源于 “山海相逼” 的生存环境 —— 耕地有限则需精耕细作,直面沧海则需勇毅坚韧,这种品格被诗人融入七言律诗的 “刚柔并济” 之中:格律的 “刚”(严谨的平仄对仗)承载 “坚韧” 的内核,诗意的 “柔”(细腻的情感表达)传递 “务实” 的温度。《痴心未改》“岁月笑吾老愈坚,退职岂肯负流年”,“老愈坚” 直白写出莆田人 “不服老、敢担当” 的坚韧,而 “退职不负流年” 的表述,又藏着 “不尚空谈、重实干” 的务实;《破境》“穷途岂是路终章,目蕴星芒意未央”,“穷途不终” 的信念,恰是莆田人 “遇困不馁、向海而生” 的坚韧品格的诗化表达,而 “目蕴星芒” 的细腻描摹,又让这份坚韧多了 “心怀希望” 的温度。
诗人对 “崇文重教” 传统的书写,更体现出地域精神与古典诗词的深度融合。《退居寄怀》“不向浮名寻慰藉,唯从文字觅知音”,“从文字觅知音” 既是个人精神追求,也暗合莆田 “耕读传家” 的传统 —— 莆田人历来重视 “诗书继世”,即便退居,仍以文字为友,正是对 “崇文” 基因的传承;《六十抒怀》“笔落成章才情显,文成数语志飞扬”,花甲之年仍保持创作热情,不仅是个人 “老当益壮” 的写照,更折射出莆田 “崇文不辍” 的文化氛围。这种将地域精神融入 “言志” 传统的书写,让七言律诗成为 “地域品格的载体”,既彰显了莆田文化的独特性,又因 “坚守热爱、重视精神” 的普遍主题,引发不同地域读者的共鸣。
从山水意象的文化隐喻,到民生关切的传统延续,再到精神品格的格律化表达,张元坤在《律中寄潮》中完成了对莆田 “壶兰文化” 的诗性转化。他没有将地域文化当作 “展览品”,而是将其拆解为可感的意象、可共情的关切、可传承的品格,融入古典律诗的肌理之中 —— 让 “壶公山”“木兰溪” 不再是地图上的符号,而是藏在 “翠柳含烟”“金波涌浪” 里的文化记忆;让 “务实坚韧” 不再是抽象的标签,而是显在 “老愈坚”“志未央” 中的生命姿态。这种转化既守住了地域文化的 “根”,又让其在古典诗词的滋养中生出 “新枝”,为地域作家如何用传统文学形式传承本土文化,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创作范式。
发布于:福建省配资天眼-南京股票配资网-浙江配资网-场内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技巧网站 上周美股大幅上涨
- 下一篇:没有了